【写在前面】2015年12月至2016年7月,我走访了美国19个州、三十余所学校,浸入式采访了百余位赴美留学生,零距离记录下他们在海外经历的成长与彷徨、身份认同与文化碰撞,结集为《新留学青年》。
本文原题《纽约是我的家》,是《新留学青年》中的一篇。
从“纽约文化沙龙”出来,一名头发短到近乎秃顶、身着西装的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个头不高,微微有些驼背,在活动室门口一边慢悠悠地踱着步,一边打量着四周的来客。如果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个小老头。
“哟,廖元辛,好久不见。”我听见他这样招呼道。
睁大眼睛,我又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遍。不错,是吴刚——尽管整个人沧桑了不少,脸上的胡须也开始浓密起来,但那份孤傲劲儿到底没有变。
“我以为你回北京,或者去香港了。”我说。
“回不去咯,我在纽约都八年了。”听我提起北京,他略带自嘲似的笑了笑,摆出了一个“八”的手势。“都八年了。”他嘘了一口气,喃喃地又重复了一遍。
如果不是沙龙上的这次偶遇,我几乎已经忘了吴刚的存在。事实上,我们的上一次见面还要追溯到五年之前,也就是他来纽约就读哥大的第三年。那时我因为一次开会外出,临时需要把行李寄放在纽约,便辗转联系到吴刚。吴刚的宿舍并不宽敞,与我也谈不上熟识,但还是热情地招呼我过去。
“就放两天,我后天就回来。”我说。
“放放放,赶紧放。”吴刚一边从我手中接过拉杆箱,一边爽直地说道。
卸下行李,吴刚给我倒了杯水,开始了和我的第一次详谈。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在皇城根下长大,又在纽约留学,自然少不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式的议论。吴刚也是——我去的时候,在哥大主修金融的他正沉迷于研究地缘政治,宿舍的桌上摆满了各种有关冷战和比较政治学的书籍。桌前的墙上悬挂着一张巨大的世界地图,上南下北的设计让人乍一看有些不适应,但吴刚却略带神秘地解释说:“有时候把东西反过来看,可能会有新的发现。”也许是难得碰上我这样的正在国内读政治学的朋友,他的谈兴格外地浓,一会儿聊起次贷危机后中国的发展战略,一会儿又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起他正在领导的Global China Connection的活动,问我国内高校的学生是否也有兴趣加入。我接过他们自己制作的传单和手册,反反复复研究了半天,又听吴刚详细讲了一通,到底没听出个所以然,最后还是婉拒了。但无论如何,那时他的意气风发,GCC在校园里做宣传的浩大声势,还是给我留下了十足的印象。
但自那以后,我们的联系就渐渐少了。一晃五年过去,我们在沙龙重新接上头的时候,吴刚已经在纽约安顿下来。他在一家知名的投资银行上班,去年还在曼哈顿岛靠近东河的第二大道上买了房。在经历了与前女友“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纷争后,他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两人的感情和谐融洽,正向婚姻殿堂的方向稳步前行。当我提起当初他为GCC的扩张而到处呼号奔走时,吴刚露出了一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式的表情,摆摆手说:“以前喜欢做学生活动,搞network(社交)。现在吧,喜欢静。”
大概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坐在离他公寓不远的一处茶楼里,展开了我们之间第二次较为详细的交谈。那是一个阳光和煦的周六下午,吴刚从附近的超市买菜回来,准备回家给女朋友做饭。他穿一件淡绿色T恤,一条浅色七分裤,脚上踩着老北京风格的“千层底”布鞋,看起来比上一次见面时轻松不少。提起我正在采写的访谈录,吴刚一边斟着茶,一边说:“我其实也想写点东西呢。曹桂林不是写了个《北京人在纽约》嘛,我就想啊,我来纽约八年了,不如也写一个,叫《纽约是我的家》。”
“家在纽约”的吴刚缓缓地放下茶壶,开始讲起这八年来在纽约生活的感受。他的讲述中英文夹杂,讲到兴头时,往往用一长段英文的排比,有一种说唱歌手似的节奏感①。
我在纽约八年。但我性格上不是那种常去夜店的人,不像现在很多网红公众号,那帮小姑娘一上来就“啊,伟大的纽约”(笑)。我没有那么多讴歌。很多人读了两年书要走了,离开纽约的时候写挽歌,说哎呀我要离开纽约了,说这儿多么伟大,我体验了纽约——吃也好,玩也好,各种高大上的东西也好,残酷的社区也好。曾经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景儿,我刚来纽约的第一天还专门跑到街上去吃热狗,去买耐克鞋,觉得自己特美国。但现在我不觉得,我觉得稀松平常,You can be anywhere(你在哪儿都一样)。对我来说,这个城市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像一场盛大的聚会,而更多的是生活中的细节和片段。比如街角的某家咖啡店,比如那边的秘鲁领事馆——我当时去那儿办的签证,然后花了四天徒步登上马丘比丘。
要说纽约最迷人的一点,那肯定是包容和多元性。无论是职业发展、艺术、政治还是吃吃喝喝,那么多的选择都会让你觉得兴奋,会觉得哪里都有机会,This is the empire state of mind②。你也会遇到各种人,也包括老纽约人。比如在公司里做行政的大妈,她会告诉你“9·11”那天她正好从世贸中心旁边经过。比如在我们家旁边遛狗的一个大爷,抱着一只小白狗,告诉我说他曾经在百老汇唱歌。我问他演过哪出剧,他说八十年代的时候演过《西区故事》,然后“腾”地就从长椅上站起来,“哗哗”地给我来了一段十分钟的唱段。纽约是可以活得很孤独的,People have to stay relevant in their city(人们在城市里总需要一些存在感),这些人需要出来给自己找点事做,找一个群热络一下,或者找一个人来分享他们的生活。
但说实话,这些都是表象。你要是真的在纽约待久了,就会明白,It's really hard to settle down in New York City(在纽约安定下来真的很难)。在纽约的压力有多大?有一句话叫作 “Everyone is fighting everything”(每个人都在与每件事搏斗③),我觉得特别贴切——无论是工作、通勤、住房,都是这样。作为中国人,职业道路上也确实存在着“玻璃天花板”,因为这个社会还是很现实的,说白了,还是一个看脸、看背景的社会。
而且也分圈子——这个也是我在工作之后开始认识到的。你看纽约好像那么大,那么丰富,其实都是分割成一个一个圈子的。和其他很多城市相比,纽约好在它不看你的背景——你从哪儿来并不重要。但它又和加州不一样,加州可能会更开放,但纽约是有一个establishment(建制)的,它是分层级和圈子的,人们基本上只和自己有相似背景、相仿年龄的人一起出去。在纽约我见识过在长岛长大的移民、在纽约搞“民运”的老留学生、所谓的侨界领袖,哈佛毕业的银行家——他住的那房子价钱超过两千万美元,共和党的议员经常在那儿集会。这都是要分圈子的。像纽约的金融圈子——我说的是在一级市场的那帮人,都住在(曼哈顿)岛上,去一样的酒吧,讲同样的笑话。在这个圈子里,我作为young professional(年轻职业人),领着一份不错的薪水,说着流利的英语,美国人也会觉得,嗬,你看这中国小伙儿,哥大毕业的,精力充沛,又聪明,他们就会愿意跟你聊。但你可能依然融不进更本地的圈子,比如他们聊奥普拉④,驾着游艇出海,也不会喊你。当然我自己呢,心态也比较好,我不会太和别人比较,尤其不会和那种金发碧眼、哈佛毕业、现在在黑石⑤的美国人比较。他们那样的美国人,可能在爷爷辈儿就在做投资人了,咱跟他不在一个级别。
屁股决定脑袋,你处在什么位置,就会有什么样的圈子和主张,而且在圈子里待得久了,你也会慢慢地变成那样的人。我不知道这么说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庸常,但我觉得庸常也没有什么问题。我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我会去关心我的工作是否稳定,因为我的圈子、我的生活质量、我的消费、我的闲暇时间,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我的工作是否稳定。以前在哥大的时候,我还经常搞点政策研究,还想辅修政治学。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狗屁。我现在的生活越来越……这么说吧,就是更少地关心别人的生活,但更多地去想怎么样更好地养家,去想未来有了孩子之后,怎么样给他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就拿旅行来说,我之前自己去秘鲁去马丘比丘,我背着一背包就去了。但我要是带着老婆孩子去旅行,我总不能再住一爬着虫子的旅馆,你说是吧?
前几年有一个电影《革命之路》对我触动很大。它这个革命是在说什么?其实就是说美国的中产阶级生活稳定了,有房子有车,对伴侣、对生活的激情都已经没有了,那怎么办?在大纽约地区,尤其是康涅狄格⑥,这样的人有很多,包括在纽约的中国人里面,也有很多。我曾经特别怕成为我看到的这么一群中国人——每年拿着30万到50万美元,家里一个老婆两个孩子三条狗,开着两辆车,周末搞个同乡会你当个会长我当个副会长。我特怕和他们一样,没劲了,生活没劲了。我都能想象出那种状态下的我——在高速公路上看着新英格兰灰蒙蒙阴冷冷的冬天怅然地哭出来,我都能想象出来。但是现在我不会,我很佩服那帮人。他们能做到那个位置,那是年轻的时候加倍地努力,比美国白人更努力地干出来的,他们配得上现在的享受。
我现在把纽约看成自己的家。北京是不是家?当然是,但是你要知道,我现在看北京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这八年来我每一次回北京,我站在繁华的大街上,我都觉得,我不知道我要去的方向。我在纽约不会——我从机场出来走进地铁,我闻见地铁里那一股尿臊味儿都觉得,这是回家了(笑)。但话又说回来了,我能把纽约看成自己的家,那是因为这个城市还是给了我一席之地的,我的技能让我在纽约有施展的空间。说白了,如果纽约不承认我,我也没法儿管纽约叫自己的家——我只能管“中印新村”叫家(笑)⑦。
什么时候在纽约扎下的?这么跟你说吧,我是找工作找到暑假实习的那一刻,那一刻——我觉得在纽约扎住了。我印象很深,那是一个虎年的年三十,那时候次贷危机刚过,全学校的人都在找工作,我找工作也找得焦头烂额。结果到了兔年的第一天突然峰回路转,“啪叽”一下来两个offer(录取信)。我们哥大的那帮人知道了之后,也都惊了,因为那时候在纽约做投行的中国人很少,不像现在,中国人的孩子都进来了。当时自己牛哄哄的,觉得总算被recognize(认可)了——就好像晚餐桌上总算有了自己的位置,虽然那个位置可能并不起眼,但总算是有了位置。
但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完全把纽约当家。上大三的时候,有件事我印象很深。我跟着你们北大的一个校友吃饭,他在这边做基金,做得很成功,而我当时还是一毛头小伙子,什么都不懂,很狂。他在“山王”——很好的一家餐馆请我吃饭,吃了一百多块钱(美元)。他说我也是北京人,但我也认为自己是纽约人。那一刻我觉得很惊讶,一个北京人跟我说自己是一纽约人,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直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会认为自己是个北京人,或者至少是亚洲人,将来即使不回北京,也会去香港,和我的(学金融的)同辈一起去拼。三年前,六年前,我都以为我要离开了。大三收到offer的时候我发了一条微博,我说三年过去了,现在要再干三年了,我说“在纽约的下半场要开始了”。等到五年过去的时候,我心想,哈,估计要结束了。结果现在来看,那根本就不是下半场,换了一个工作,又是三年。
到现在毕业都四年了,大家用脚投票,有些人走了,有些人留下了。为什么能留下?还是因为有这个实力。你的生活稳定了,很多事不再想了,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了,去留在于自己了,有了选择的权利,这才叫家。家是什么,应该是一个舒适的地方,一个提供安全感的地方。我虽然存不下什么钱,但是如果你现在让我住在一特别破的地方,每天上下班在地铁里挤半个小时,那还是拉倒吧。每天下班坐到法拉盛⑧,住在一个四百块钱的屋子里面?那不是家,那是奴隶。
由于是闲聊,吴刚的叙述略微有些散乱,往往一个话题还没有结束就跳到了另一个,让我一时间有点应接不暇。但聊到最后,他对于“家”的定义,以及“我现在把纽约看成自己的家”的表述,还是让我竖起了耳朵。在提到“纽约是我的家”时,他特别强调,他所谓的“纽约”,仅仅指的是市中心的曼哈顿岛,而不包括广义上的布鲁克林、皇后区、布朗克斯、长岛或者哈德逊河对岸的泽西城。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我来美国八年,没有过一天乡村生活——都不只是没有过乡村生活,我是八年都在曼哈顿”一直是吴刚津津乐道的话题。
看得出,工作的稳定、收入的增加,以及在职场圈子中的日益融入,已经让吴刚“反客为主”,开始有意识地在自己与千千万万的“纽约客”间划出界线。对于后者来说,“体验”就是一切——尽管他们并不一定是华尔街、百老汇、大都会博物馆或者纽约时装周的真正参与者,但只要与它们“共处一市”也是好的。为了“感受世界与时代的脉搏”,他们不惜一边抱怨着狭小陈旧的住房,一边对动辄晚点和改线的地铁忍气吞声。但吴刚不一样。尽管他也曾经是“纽约客”中的一员,也承认自己曾经“就是一个愣头青,什么都不懂”,但随着经济实力与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在“只有真金白银将身份量化成数字了才叫实现美国梦”的纽约,他已经完成了“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去留在于自己”的蜕变。而他的那句“我每一次去‘中印新村’,都觉得很压抑”,以及带着几分夸张语气脱口而出的“每天下班坐到法拉盛,住在一个四百块钱的屋子里面?那不是家,那是奴隶”,无疑正是这种蜕变的最佳注脚。
“‘漂泊者’其实是不被看见的,被看见的只有成功者。而只有成为主流的成功者,漂泊才具有意义。”在分析当代中国的两种青年主体时,王翔曾这样评论道。毫无疑问,吴刚是“主流的成功者”,而也正是因为这种“主流”意义上的“成功”,让他对于纽约产生了归属感,开始对这座“来来往往都是客”的像一座巨大的中央车站不断吞吐着人流的城市流露出“家”的感情。然而另一方面,“经济决定论”又并非是解释这种归属感的唯一可能。事实上,面对我提出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纽约是自己家”的问题,吴刚并没有一下子给出“是在我第一次领到薪水,觉得要开始对自己负责的时候”的回答。在思忖再三并最终做出回答之前,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用英文脱口而出:
我第一次接吻是在这儿。第一次拉女生的手——在9街和第六大道的路口,是10月的一个周六。第一次拥有工作是在这儿,第一次交水电煤气费是在这儿。第一次拥有自己的一辆车是在这儿,我第一次学车也是在这儿——路考我考了三次才过。第一次撞车也是在这儿——我把一辆停在路边的车撞了,在大雪中等车主等了一个半小时……
“也许可以说,你第一次独立地探索人生就是在这儿?”我问道。
“没错,你说得没错。”吴刚的语调扬了起来,“可以这么说,我在纽约其实就没有好好读过一天书,因为我读的是一所社会大学,一所叫纽约的社会大学。”
如果从今天的角度回想,大概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开始理解吴刚内心深处对于“家”的定义——尽管在正襟危坐时,他对于“家”的解释往往有着更明确和狭隘的指向。也大概是在这一刻,我才开始意识到吴刚那句“我现在看北京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中那“有色”的含义——尽管在我问起那是一种怎样的“色”时,吴刚自己也难以言喻。事实上,如果说吴刚前十八年在北京的成长经历是一个接纳生命和继承现有生活的过程,那么纽约则是他亲手创造生活与重新认识自我的所在地。在八年这样的探索和社会化过程中,他观察世界的瞳孔前已经渐渐架起了一副名叫“纽约”的眼镜。戴得久了,这观察的途径与观察的对象竟渐渐融为一体——透过它,他观察着社会,也审视着自己。离开它,他站在北京熟悉而繁华的大街上,却感叹“不知道要去的方向”。
“我现在要是想回北京的话,很容易。北京有房子住,有朋友,随时可以回去。”在我们分别的时候,吴刚笑着说,“我呀,还是等中年危机的时候再回去吧!”
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在“中年危机”之前再也见不到吴刚了——或者不好意思地说,我几乎又一次忘记了他的存在。但我终究还是见到了他。在我们分别一年之后,在北京哥大举办的一次活动现场,我注意到一位头发短到近乎秃顶、身着西装的男子。他站在场地的最后一排,手上端着一杯咖啡,对主讲人的发言似听非听的样子,显得有几分疏离。我走近一看,是吴刚。
“搬回来了?”我问他。
吴刚略带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搬回来了”。
是因为工作签证到期,公司外派回国,还是因为马上要结婚的缘故?我没有再仔细问。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个问题已无足轻重。我只是注意到,在微信头像的照片上,一身深色西装的他,与身着红色套裙的未婚妻站在北京的鼓楼前,手牵着手,仰望着屋檐与天空。鼓楼墙壁上那古旧的、平日看起来甚至有几分灰蒙蒙的红色,此刻却仿佛一个大大的“喜”字,显得年轻而绚烂。
注释:
①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段叙述中,吴刚有约三分之一的地方使用了英文。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统一译成了中文,仅保留了若干具有鲜明表达效果的英文原话。
② Empire State of Mind是由美国说唱歌手Jay-Z和女歌手艾丽西亚·凯斯演唱的怀念纽约生活的歌曲,歌词中有“纽约,摩天大楼堆砌筑成的梦想。现在你身处纽约,你已经无所不能,纽约街区让你浴火重生,纽约霓虹灯让你热血沸腾”的表达。
③ 有朋友建议译作“人人都事事忧心”或“不拼者无立锥之地”。为了阅读方便,我在文中保留了直译的译法,但这两种表达亦请读者参考。
④ 指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美国著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亿万富翁。
⑤ 指黑石集团,美国著名资产管理公司,总部位于纽约。
⑥ 康涅狄格州与纽约州接壤,不少在纽约工作的中产阶级和富人都住在康涅狄格州。
⑦ 指与纽约市隔哈德逊河相望的泽西城(Jersey City)。由于不少在纽约上学、工作的中国人和印度人居住于此,当地的中国留学生戏称其为“中印新村”。
⑧ 法拉盛(Flushing)位于纽约皇后区境内,近年来成为亚裔移民特别是中国、韩国等地移民聚居的地方,并发展出具有浓厚东亚风味的商圈,商圈发展程度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的国内三四线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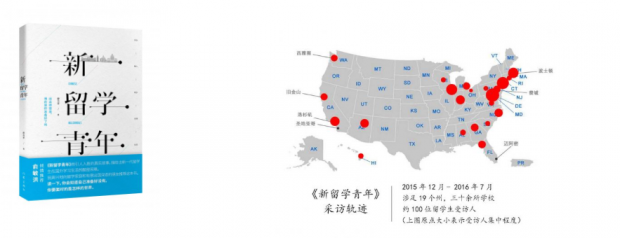
作者廖元辛,北京大学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专业,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硕士,财新前记者。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